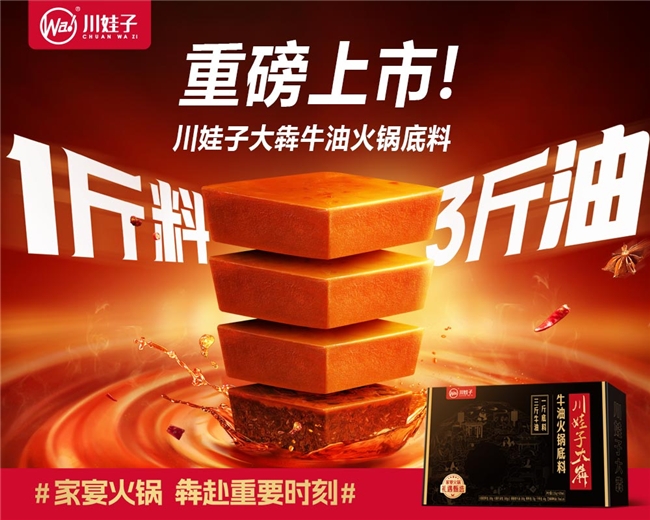馬伯庸:你對美食的態度就代表你的人生態度1

馬伯庸擅長撰寫歷史題材的文學故事,他的故事不描述戰爭或國家,也不聚焦英雄偉人,而是將筆頭對準小人物,撰寫宏大歷史下他們的個人記憶和生命體驗。他的多部小說被改編成電視劇,《長安的荔枝》《大醫》《顯微鏡下的大明》《長安十二時辰》......甚至有了“馬伯庸宇宙”的說法。
馬伯庸就是這么一個拿捏細節的好手,能把一段幾行字的史料擴充成一本精彩紛呈的好書。新書《食南之徒》也是如此:以美食為線索,朝堂詭譎,風起云涌,甚至淪到殺頭掉腦袋的危險境地,主人翁也能因一盤美食轉危為安,除了感嘆吃貨好運外,也被劇情線調得十足十。
帶著對歷史的好奇和對美食的向往,我們采訪了馬伯庸。在被問到“對于一個作者來說,寫‘吃貨’的故事需要自己也愛吃嗎?”馬伯庸毫不猶豫:吃對于我來說是人生大事!
《食南之徒》
“吃貨”的私心
馬伯庸是個老饕,幾乎嘗遍了大江南北的美食。他說自己愛吃,吃對他來說是人生大事。
“我覺得對于美食的態度就一定是代表了對人生的態度。你對美食的要求高,說明你要過一種精致的、松弛的、可以靜下心來摒棄掉一些俗務、專心去享受的生活態度。我覺得對于現代人,尤其是現在的都市人來說,這種態度彌足珍貴,它能夠幫我們治愈,或者抵御很多都市病。”
因此馬伯庸一直想寫個和美食有關的故事,直到前不久,《食南之徒》出版。
書中提到的美食得都是馬伯庸自己吃過的。“只有吃過才知道它的味道和獨特在哪,寫美食最難就在于一定要寫出它的獨特性,不能簡單地用‘入口即化’‘色香味俱全’這樣泛泛的描寫,只能是自己親身去體驗。”馬伯庸說。正因如此,我們才能在書中讀到他寫西江的嘉魚——“筷子一觸到魚身,魚肉竟自潰散開來,只見肉色如白璧無瑕,只在表面浮動著一層淺淺的油光。”光是短短幾句,就讓讀者不禁食指大動。
《食南之徒》內頁插畫,作者:施曉頡
馬伯庸年輕時在廣州待過,對廣州有感情,對廣州美食更是念念難忘,“包括現在每年我也會專門去廣州,廣東這個地方本身它就是一個美食大省。那我又是個吃貨,其實是把我對廣東美食的感情寫到書里去了。”聊起吃美食故事,馬伯庸滔滔不絕,舉了個廣東肇慶的朋友故事。一次友間喝茶,馬伯庸提起想寫一本關于廣州美食的書,問有何推薦。朋友聽了眼睛一亮,提到“裹蒸”,“他二話不說,擼著袖子就要出門給我買,然后給我從頭到尾講這個東西的特點是什么,還有用冬葉裹上之后不容易變質之類的很多細節。朋友說的細節是我上網查資料查不到的,只能是通過當地人親自吃過講過之后才知道。”
就這樣不帶遮掩的,馬伯庸將自己貪嘴的美味悉數置于書中。“我自己偏愛牛雜。我每次去廣東一定會去吃牛雜豬雜這些雜碎類的東西,所以我在書里,也濃墨重彩地把它作為重要的菜肴寫進去。”
《食南之徒》內頁插畫,作者:施曉頡
歷史的由頭
寫美食,但馬伯庸的美食一定要有故事、跟人物命運緊密相連,這就得有一個由頭——《食南之徒》的“由頭”就來自一次在廣州南越王宮博物館的意外所得。
展廳里有兩枚從南越王宮水井里出土的竹簡,仔細辨認了才知道寫的是“壺棗一木”字樣。這是兩棵壺棗樹的園林檔案。但是南方本沒棗樹,棗樹哪里來?原來南越王趙佗是北方人,南渡后思鄉心切,于是在南方種了北方家鄉的棗樹,以解鄉愁。竹簡上短短幾行字落到馬伯庸的心里,成了一本精彩小說的敲門磚。門,就這么打開了。“它本身并沒有太多信息量,但竹簡背后有很多的歷史和想象空間,你可以推想出很多的當時的一些人的情緒、人的故事,它有很好的延展性,我覺得找到了一個契機。”
《食南之徒》內頁插畫,作者:施曉頡
寫書的契機落得巧妙,但過程也有秘辛。書的構思和前期資料搜集,持續了4個多月,看起來輕巧似乎從跟“全國各地朋友聊天”里得來素材靈感,實際上是個四兩撥千斤的竅門,招招貼著蛇的七寸打去,恰如其分的。《食南之徒》寫的是西漢的故事,寫西漢年間美食馬伯庸有兩個原則:一是寫的食物一定要是現有的,因為“現實的連接感很重要”,“大家看完書或者看書看到一半拿起手機就能叫外賣,就能吃到。好多讀者跟我講,他們看一章,就把這一章提到的美食點外賣或者在家里做來吃,解決一下自己口腹之欲”;二是寫的美食要符合史實,
“只有在西漢年間它的烹飪方式已經存在,它的原料已經傳入中原,那么我才寫。《食南之徒》的開場烤的是兔子和雞,因為那時候羊肉很難傳到南方,牛則屬于重要的生產動物不能隨便吃......。”
“美食中也會有懸疑,美食也可以來講政治。李安的《飲食男女》拍的并不僅僅是飲食,陸文夫的《美食家》,寫到底寫的是人生態度。所以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無法歸類的。一個好的故事,沒法用簡單的標簽來歸類,它一定是多種要素的復合。”
誠然,好故事難歸類,但酣暢淋漓地順暢寫下去,就像一盤好菜,色香味俱全,還留有余味,讓人下肚后,隔了十天半個月,還會懷念再三。
Q
你的作品都是基于歷史的某個點, 是對“歷史可能性小說 ”的探索 。這種基調有可能發生改變嗎?將來有可能寫一篇發生在未來的科幻小說嗎?
馬伯庸:我是覺得創作,用一個已經特別俗套的話說,就是要“接地氣”,說白了就是我們要了解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是什么,他們關心的是什么,厭惡的是什么,焦慮的是什么,不僅我們要寫現代都市小說才能用得上,實際上寫任何作品都用得上。對我來說寫歷史小說最大的樂趣就是在于我能夠把古代具有現代性的東西提煉出來,展現給你們看,同時又不違背我所堅持的歷史邏輯和歷史真實這兩個原則。
為什么《長安的荔枝》大家愛看,是因為我們看到的不是運荔枝的過程,而是看到的是一個社畜,接到了一個不可能的活,怎樣排除萬難把這個活干完。《長安十二時辰》為什么很多人愿意看?也不是因為大唐他們才喜歡,而是因為他看到一個刑警隊長為了保護市民的安全,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我們的歲月靜好是因為有這些人負重前行。每一個作品不管是現代的科幻的歷史的,它最終都是要打動現代人的內心的一個柔軟的地方,我們要找到和現代人的共鳴,這部作品才能夠被更多的人所認可。所以說不管是歷史也罷科幻也罷,為什么大家那么感動,那是因為跟我們現實生活密切相關的。我寫任何作品一定會想這個東西普通人感動的點在哪里,普通人能不能跟他產生一種共鳴?找到這種共鳴了,任何題材都有可能創作出經典。
Q
你曾經提到過, 寫作是業余愛好, 有興趣才去寫。現在作為職業作家的你還會說“ 寫作是愛好 ”嗎?保持熱愛的秘訣是什么?
馬伯庸:
我一直認為,作家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狀態。你有表達的欲望,并且付諸文字,你就是作家,當你停筆不寫了,就不是作家。歸根到底,作家是靠荷爾蒙寫作的,如果沒有激情的話,寫什么都沒勁了。咱用通俗的話說,寫東西其實是愛得瑟、愛顯擺,這種顯擺和得瑟不會因為你收入變化而變化。如果說我寫完了,功成名就了,我就安心享受目前的這些稿費,這種生活我現在想象不出來。
像寫《長安的荔枝》的時候我第一次碰到一個絕無僅有的,心理學上叫做心流的狀態。那天我特別興奮,過得沒日沒夜的,不按正常的社畜的時間來了,抓起電腦就寫,而且腦子里想法拼命涌現出來,手都寫不過來,一口氣11天把它寫完,寫完之后整個人就有點虛脫似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可以說《長安的荔枝》我是花了11年寫出來的。前面這11年里,我在關心唐代的一些考古報告,關心吃喝拉撒服飾交通各種生活細節,包括我去各地簽售或者去參加活動會關注各地的風土人情。我日常會保持一種好奇心去看各種事物,經過11年沒有目的性的積累,到了爆發的點,忽然之間我就不用再去查資料了,所有的資料我都諳熟于胸,把它迅速地寫出來就夠了。《長安的荔枝》是一個特例,但是這個特例背后其實是一個我多年來的習慣,對所有的事情保持一個好奇心。我覺得好奇心對于創作者來說是最關鍵的。保持一個足夠的好奇心,愿意去深入挖掘,你就能挖出很多八卦。這些八卦現在可能沒有用,被我記錄一下就放在那里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變成了我的寫作素材。
Q
在當今,大家好像不看書了,和閱讀比起來,短視頻更有誘惑力。你怎么看這件事?如果要你給年輕人幾個閱讀建議, 你會說什么?
馬伯庸:古人有句話,什么時候看書,“馬上、廁上、枕上”,沒有一個場景是在書房正襟危坐看書的。以前閱讀要帶一本實體書,隨著科技的發展現在只要帶個手機,里面可以有一排閱讀軟件。就算不看書,也可以聽書,這也是一種獲取知識的渠道,也是一種閱讀。對我而言,我想要的是書里面的內容,而不是它的載體。所以我不覺得現在大家看書少了,反而覺得大家看書多了。只不過現在大家焦慮看書有什么用,能給自身帶來什么樣的提升、解決生活中的什么困難,我認為這個心態要調整。看書不解決問題,尤其是看閑書;但從長遠來看,看的閑書有朝一日也可能會變成人一個閱歷,在你碰到困難的時候,一下子想起來、用得上。
從古至今,除了專業閱讀外大部分的日常閱讀都是碎片化的。之前網上有一句話我特別贊同:碎片化閱讀像竹籃打水一樣,即竹籃接過去,水嘩地一下全漏得干干凈凈,一滴不剩,但是籃子卻洗得很干凈。碎片化閱讀就是這樣,好像看完什么都沒記住,但實際上你還是在接受某種潛移默化的影響。當碎片化閱讀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發現自己好像成長了些。因為再怎么碎片化,它也是一種主動閱讀,需要你邊讀邊思考,讓腦子主動去做事情,這就是它的意義所在。
針對閱讀,我有個有點矛盾的建議。一方面,我建議大家閱讀帶一點功利性,這其實來自蘇軾的“八面受敵讀書法”,即你要帶著問題、帶著目的去看書,這樣才能有的放矢,知道自己要解決什么。這種方式能讓你在讀書的時候效率很高。另外一方面,讀書又不要太功利,不能只是有事了才去讀書,沒事的時候也要讀。
Q
和我們分享一些對你的寫作和生活產生很大影響的書吧!
馬伯庸:寫作者看書往往會從創作者的角度出發去思考,關注如果我是作者我該怎么寫、人物怎么發展等等。
我小時候看的哲學書《蘇菲的世界》,它沒有平鋪直敘地講亞里士多德、孔子的生平,而是通過蘇菲這個人物,像魔幻故事一樣把他們展開來講。當時作為讀者的我覺得很新鮮,但二三十年后我作為作者再去讀,我關心的是作者怎么把那么艱澀的哲學思想通過這么平易近人、有趣的方式展現出來,他是怎么展開腦洞把它寫成一個完整故事的。
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對我影響特別大。它里面提到過一個觀點,說明朝是沒有數目字管理,或者說中國古代沒有精細的數目字管理這種方式,所以導致了統治的一系列的問題。我讀后大受震撼很有感觸,因為一般來說我們聊明朝,會聊他的政治格局,聊他的經濟狀況,或者聊他的軍事變化,但是很少有人會細到管賬算賬的這個事情。其實后來隨著我對于歷史研究的深入和認知,我現在不認為黃仁宇先生這個觀點是對的,明朝其實他的數字管理還是挺精細的,他的問題不在于數字本身。但是這本書提供的這種視角會讓我覺得耳目一新。
左:《蘇菲的世界》,作者: 喬斯坦·賈德;右:《萬歷十五年》,作者:黃仁宇
我們歷史中耳熟能詳的東西背后其實都是在算賬,都是錢。不光是歷史,現在也一樣。你會看到所有的歷史故事,所有的現實世界,如果深入挖掘他到底為什么這么干,最后發現真正的原因都和錢有關系。我前一陣開玩笑,我說我人過四十以后越來越愛錢了。人過四十之后,我感覺會變得越來越現實,會關注到現實中很多的底層運作邏輯和規律,所以會不由自主地去看經濟類、政治類和哲學類的書
。不光是我,身邊朋友過40之后都會或多或少地拿起這些書來看。我覺得這也是人生的一個必經階段。
所謂“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覺得說的就是當你40歲之后就會不由自主地去尋找一些規律,來解釋自己過去40年來所經歷的事情,要不怎么說中年人“爹味”比較重呢!我每天都覺得自己找到一個規律,但是我時刻告訴自己,你不要“爹味”那么重,覺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大徹大悟了,還是要持續看書,這樣才會發現你的一些想法還很淺薄。而所有這些書,最后也可能會變成我創作素材的一部分。
讀歷史也是非常好的。讀歷史讀多了人會越來越開通,或者說越來越心態好。很多時候你覺得想不通的事情,在看到歷史上的很多解釋之后,你會發現原來它是有原因的。很多時候我們的焦慮是來自于我們的不理解,這件事情你為什么要這么做?你憑什么來害我?但是你度過歷史之后你會發現那些壞人背后都會有利益的動機,你就知道他們其實也不是針對你,他們只是要截取更大的利益。那么你到底是要攔他一路,還是說你要同流合污?那當然就是個人的自己選擇。我覺得讀歷史最主要的就是能讀到一種清楚的解釋,當我們把這個世界看得清楚了之后,我們就能夠對很多事情就釋懷了。另外讀歷史能夠給我們自己在現實中的行為找到一些根據,找到一些借口,找到一些能夠舒緩的空間。
說“讀史使人明智”的原因就是這事我看開了,我未必能夠做決定,我未必能夠做主,但是這件事情我至少內心我能夠和解掉,不會糾結于此。
內容源于《周末畫報 Reading Life》
采訪、撰文 — 劉小荻
編輯 — Emin
特別鳴謝 — 博集天卷
冷鏈服務業務聯系電話:19937817614

華鼎冷鏈是一家專注于為餐飲連鎖品牌、工廠商貿客戶提供專業高效的冷鏈物流服務企業,已經打造成集冷鏈倉儲、冷鏈零擔、冷鏈到店、信息化服務、金融為一體的全國化食品凍品餐飲火鍋食材供應鏈冷鏈物流服務平臺。
標簽:

 冷鏈新聞
冷鏈新聞 企業新聞
企業新聞 展會新聞
展會新聞 物流新聞
物流新聞 冷鏈加盟
冷鏈加盟 冷鏈技術
冷鏈技術 冷鏈服務
冷鏈服務 冷鏈問答
冷鏈問答 網站首頁
網站首頁 冷鏈新聞
冷鏈新聞